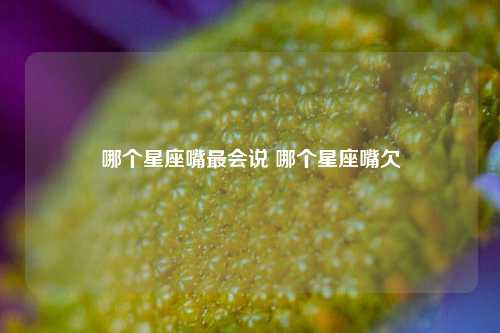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张李俐 彭茸雯 丁超逸
孙红英七十岁,进医院时没敢脱下骑电瓶车戴的头盔,尽管里面还戴了双层口罩。
这是4月10日。前一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6例,无症状感染者23937例,多数小区还“封控”着。疫情中的上海没有出租车,她开着电瓶车一路往北走十五公里,穿越两个区,到这家三甲医院给丈夫配几种精神类药物。
“封控”中的小区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出门,但居委会对接的“社区医院”找不到孙红英老伴需要的药,居委会的人只好“特许”她上路。出发之前,他们提醒她,“医院现在危险”,之前,有小区志愿者去大型医院帮居民配药,回来做核酸变“阳”了。
类似孙红英遇到的,在疫情中,上海的部分居委会只能帮居民到俗称“社区医院”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但很多常见病药物难觅踪影。
社区医院还有额外任务,医护抽调去方舱、隔离点,外出做核酸。受访的一位居委会主任每周去社区医院,遇到的经常不是上次的值班医生。
疫情中,紧张工作的社区医院和急于求药的病人之间,距离既近又远。
每天数药吃、减量吃
上海疫情开始之后,李来娣的病友们“待遇”不同。她说,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们往往都认准了一种药,哪种药吃着患病的关节不疼,就一直吃。四月的疫情之中,有的药物社区医院能配到,有的配不到,仿佛 “开奖”。
李来娣“开奖”失败,在疫情中数着药吃。
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三十年了。平日里,她会去社区医院做针灸理疗,认识住在附近的阿姨们,一起治她们的腰疼、肩膀疼、脚踝疼。她很喜欢社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对方总是边做针灸,一边与她聊天,她还想要给对这位女医生介绍对象。
社区医院不那么拥挤,医生的时间充裕一些。李来娣还在社区医院签约了一位“家庭医生”。她还有高血压,定期找家庭医生开降压药。家庭医生会嘱咐她药怎么吃、有哪些副作用,很周到。
但是,她认准的类风湿疾病药物必须由免疫专科的医生开具,而社区医院未开设这一科室。李来娣每个月还到最近的二级医院验血去——更早时候,她去三甲医院看,人实在多,她能在等门诊的时候看完一整本《故事会》,抬头看还没轮到她,去书报摊买第二本。李来娣退去二级医院,那里的医生也忙,看了她的验血结果就开药,没有功夫多说几句话。
这样沉默而反复的“验血、开药”多了,她觉得自己甚至练就一双看验血结果的眼,拿到单子,先看血反应蛋白,再看血醇……
疫情开始了,李来娣住的居民楼里有几例“阳性”。她问了问居委会志愿者配药的事情,对方仅回复医院没开,别无他法。李来娣只能把本来每天吃两粒的药减到一粒。
一名担任过上海二级医院院长的专家李孝林对澎湃新闻解释,类风湿性疾病诊治比较难,目前,推荐在三级医院确诊,二级医院复诊。
学界普遍认为,基层的全科医生应当了解病人的各项病情,给予综合的医疗服务。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官方“盖戳”。2018年1月,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科医生要多“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的工作”;“全科医生有自己的特点,岗位能力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专科医生”。
但在实践中,社区医院平时既无法为像李来娣这样的患者提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疗服务,也无法为她配药,不掌握她的服药情况。在疫情中,上海各个社区普遍需要医疗志愿者逐个登记居民配药需求。
“封控”期间,社区医院难帮上忙的慢性病,除了类风湿性疾病,还有精神类疾病。在四月初,上海市级精神卫生中心配药热线不太通畅,而多家区级精神卫生中心只为此前在本机构有就诊记录的病人提供复诊。
孙红英的老伴此前尝试了多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觉得其中一家的治疗最有效果,就认准这家。他搭配着吃的精神类药物有四种,疫情中他不仅遇到没有就诊记录的问题,也不确定在其他医院能否配齐这四种药。
他还有一些心内科的问题,在一家医院装了心脏起搏器,也一直去那里配药。所以,孙红英还得改日再跑十公里,到另一家三甲医院找药。
根据近些年国家卫健委推动的“分级诊疗”构想,“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分担大型医院的压力。

分级诊疗在推进,但大医院仍人满为患。
但是,这也会遇到一些现实难题: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在老年人中十分常见,但孙红英的老伴还需去装心脏起搏器的医院复诊。
很多患常见病的病人之前会“货比三家”地看病,再认准其中一家。乔先生患有慢性胃炎将近二十年。他在几年里跑了很多医院,认准一个三甲医院的专家以后,病情才逐渐改善。他不时去复诊,和这位专家很熟。
疫情来了,他失去了安全感,在网上求助。其实,他吃的几样治胃病的药只有一样没在药店买到,但他心头仍感焦虑。
后来,他联系上了专家。专家说,那个药可以不吃,问题不大。他沉重如铁的心才放下来。
到处打听有什么门路
上海市共有近2500万常住人口,57家三级医疗机构,121家二级医疗机构。社区医院无法参与多种常见病诊治的情况下,一旦一家二级或三级医院在疫情中“停摆”,问诊、配药会变得更为艰难。
浦东郊区一居委会主任王家君告诉澎湃新闻,自己管理的两个小区是原先附近的村庄拆迁改的,这地方离海很近,离市区很远。村里人看病,习惯去小区六七公里开外、从前“县医院”改的一家三级乙等医院,这也是距离小区最近的二三级医疗机构,疫情中一些科室关闭。
王家君拿着该医院的多张就诊卡去配药,值班的护士对他说,没有门诊号,互联网医院约得很满,“你的诉求给你登记了”。
他忍不住发了脾气。“电视里刚说,大医院开放配药的。”

疫情之中,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农兴村卫生室紧急下沉了二级医院医生,药品储备由150种猛增到400种。
疫情初期,他小区的一位居民施女士在网上求药。施女士对澎湃新闻说,母亲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在社区医院看,效果不好,转到当地人习惯去的三乙医院。疫情中,她也反复在医院的互联网平台上挂号,能预约上,但没有人接单。
疫情之中,能上路的通行证特别紧俏。王家君说,自己管的两个小区有四千余居民,最严格的一段时间,只有两张镇政府颁发的通行证,而且上面写明了姓名,只能由固定的司机开出小区。这两张通行证还不能跨江,有一些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到江对岸去复诊配药的,镇政府协调出一辆面包车,开到各个小区挨个接人。他总在代病人们协调上车时间。
小区里老人很多,有的在附近的三乙医院看病,有的在浦西的医院。镇政府也解决不了这么多人需要跨江的问题。王家君很着急,到处打听有什么门路。
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在浦西上班的医生,住在附近的其他小区。医生可以隔一段时间从医院回家一趟。他开着车把收集到的医保卡送去,托他下回把药带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他才发现一些平时很熟的居民,原来有精神疾病,要持续服药。
王家君会把病人的药盒转交给社区医院便于配药。有时候配不到一模一样的,社区医院能找出一些药的替代品,但他交给患者,患者并不满意。他感到很委屈。

王家君和两个志愿者从社区医院带回来的“成果”。 受访者 供图
专家李孝林打交道的一家社区医院扛不住骤增的配药需求,有的药物很快断货,然后,社区医院和整个街道的病患一起在断续的物流中等待。
他建议,一旦发现疫情“苗头”,允许基层医院多囤一些慢性病常用药。
“(按照现在的情况,)医保是用不完的。”他说,虽然“控费”很重要,但在疫情中,医院里关了一些门诊,不着急的手术先不做了,这部分开支少了,所以不用担心囤药造成开支抬高。
李孝林接触的这家社区医院在上海疫情期间如临大敌。一开始,志愿者拿一沓医保卡去,坐半天也拿不到药。专家给这家社区医院出主意,这样效率太低,而且在疫情中,要尽量无接触配药,应当请各居委会志愿者把医保卡和纸质材料打包放在门口,护士穿两级防护服,先对这个包裹的外包装消毒,静置半小时,再打开外包装消毒,静置半小时,最后,把纸质材料拿出来,挨个对着紫外线照。但这建议提得不太及时,社区医院还是有人“阳”了。
“怎么可能改变大众的就医习惯?”
防疫亟待“强基层”,这一构想与居民想获得更好医疗服务的愿望碰撞着。
李孝林称,解决基层首诊率低的问题,唯一的路径是推动看病“一张卡”,要求二三级医院不再接受非急诊的首诊病人。患者去社区医院,社区医院或者开方,认为有必要转诊的,再到电脑上给他们安排得清清楚楚:“明天上午九点去上级医院找杨医生。”患者可能觉得不满意,要再换。但是,他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首诊医生。否则,怎么可能改变大众的就医习惯呢?
至少2011年起,上海开始尝试建立“区域医疗联合体”,允许患者在社区医院预约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包括专家门诊。但在2017年,有一名上海社区医院管理者在论文里感慨:“上海市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的情况下,社区全科医生要向二三级医院转诊签约病人其实只有一个字‘难’。”
但是,另一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录法对澎湃新闻说,在社会没有初步共识的情况下,很难推强制的“基层首诊”。
他的研究领域是公共卫生政策。在调研中,有基层医生对他说过,尤其是小儿科,一般情况下,基层医生面对患儿父母,并没有那么大的威信,对于给发热患儿降温等问题,一言不合,会扭打起来——患儿父母只听三甲医院“专家”的话。
而且,一旦要加强医院之间“转诊”的关系,有很多的关系需要厘清。采访中,一名糖尿病患者对澎湃新闻回忆,他平时经常去社区医院配胰岛素,但是,社区医院给他开的胰岛素,一次只给一两个星期的剂量。工作忙起来的时候,他更倾向于去大型三甲医院排长队,因为三甲医院能开足,排一次队,配的药就够用好几个月。
李孝林分析,各家医院都有控费要求、门诊量要求,工作各有偏重,“落实到(每个)医生”。转诊机制牵涉很广,需要考虑不同机构、不同医生、不同患者的愿望。
张录法觉得,以目前的条件看,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基于几级医院之间合作建成的“医联体”推动一些线上的诊疗中心,帮助患者在基层医院拍片、验血,上级医疗机构医生远程问诊。如此,疫情严重的时候,“(上级医疗机构的)医生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医联体”要求医生、医院之间紧密配合,与病人拉近距离,而在四月的上海,物流不通畅的情况下,病患与各家医疗机构之间的距离显得更远了。连通着病人和各个机构的,可能是居委会主任的人脉、浦西三甲医院医生的私家车和跑腿小哥。
4月25日,一名跑腿小哥对澎湃新闻说, 由于物流变慢,公司给他买的帐篷一直在路上。他有很多个夜晚睡在桥洞里。

没有帐篷,外卖小哥“席地而卧” 。
“你知道我们现在送的什么东西最多吗?”“全是药。我今天打开看了,好多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现在基本上三个药里面两个都是高血压的。”
除了叫跑腿去线下的药店买药,也有患者投奔线上。
一名京东健康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虽然京东健康在3月29日上线“药品求助登记平台”,一小时内涌入一千多条求助信息,但“京东大药房”在四月上海本地的订单量较前段时间没有明显增长。多数的求助可以就近解决,而在线上,“当(消费者)看见预计的到货时间较预期的差距比较大,就不会下单或者取消订单了。”
京东健康在上海本地没有药仓。4月22日,该公司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正在逐渐恢复外地进入上海的运力,在疫情中,线上问诊的项目会比药房业务好做,因为“不涉及线下的履约”。
她说,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京东健康的日均线上问诊量增长50%,武汉地区尤甚。
但就基层“全科医生”的供给方面,京东人士坦言,目前互联网提供的“家庭医生”基本是“日常的健康管理”,设想中并不包含疫情中的应急工作。因此,只能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一种补充。
去方舱、去隔离点、去做核酸
上海一般被认为是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但在“抗疫”的过程中,各级医院的医护均人手吃紧。
5月3日,一名社区医院全科医生刘佳对澎湃新闻说,她目前在一家方舱医院工作。约六七个医生组成的医疗组负责一个七十人的病区,其中很多是老人。上班时间,她不断地查房,写病历,方舱医院的医护住在一个较远的酒店里,上下班还得几个小时,负担不小。
据刘佳了解,由于人手过于紧张,该区域有的社区医院直接关闭。原先对接的居委会被分流去其他社区医院配药。
在疫情之前,刘佳和一名助理负责一个五六千人的小区,如有小区居民同意,担任他们的“家庭医生”。她说,社区医院在疫情中做了一些转诊工作,小区里有几名居民需要血透,他们帮忙联络了上级医院。
疫情初期,还有很多居民打她的电话,她也在上海“健康云”等平台帮助居民办了一些配药业务,但后来要去方舱支援,就顾不上了。
刘佳对澎湃新闻解释,社区医院只能进一些基础药品,也可以为患者办理“长处方”,让患者定期去二级、三级医院看病,日常在社区医院拿药。“长处方”也有限制,可以包含一些类风湿疾病药物,或者价格较高、医保与患者各承担部分药费的进口药,但不包括一些管控更严格的精神类药物。像李来娣这样原本每个月去二级医院验血的患者,平时也未必需要社区的“长处方”服务。

关于印发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居民的医疗服务要求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多,有些人想配进口药,有些人想配便宜药,但是社区不可能所有药都有。”她感到,“站在居民的角度,现在配药的确难,各种限制好多。但是站在医生的角度,有时候你的好心建议,反而会被他误解。他们宁可相信网络,也不相信医生。”
在她工作的区域,与“家庭医生”签约,并不妨碍病人去其他区的医院自由就诊。只是与她签约,她能在系统里看见病人在其他医院就诊、配药的记录,多给一些医疗建议。
可是,来看刘佳门诊的,她本来也会了解他们在专科医院的诊疗情况。实际上,有的患者认为给“家庭医生”看诊疗记录妨碍隐私,有的人觉得“没意义”。
2020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上海有“家庭医生”6000名,超800万人签约他们的服务。
在疫情中,不仅社区医院的医护工作量巨大,二级、三级医院也需要勉力维持日常门诊的运转。
4月26日,一名区级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钱进对澎湃新闻说,原先上海有一些小范围疫情,医院里的护士会被抽调,但到了今年三月中下旬,医生们也必须出动了,去基层做核酸。
这种工作十分“机动”。这名医生清楚地记得,3月一天深夜,他满心是自己的学术材料,写到凌晨——第二日,他被抽调去社区。
当时,还并不是各栋楼分别下楼做核酸,钱进坐下不动,面对的队伍漫长。有些排队的居民情绪激动,催着居委会干部,接着,居委会干部也激动起来,过来催他。
这些天,钱进被调去一处酒店隔离点工作。据他描述,十个人的医务组,服务数百个“密接”,要每日给他们做核酸;要监督酒店工作人员处理医疗废物,还要安抚“密接”者们的情绪。
由于奥密克戎潜伏期短,对“密接”人员的观察期由十四天缩短到七天,再到五天。这意味着,为他们办理出入手续的医生工作更忙。医生总是提前在酒店楼下坐好,等待转运车辆。
据他了解,他的同事们有的在隔离点,有的在方舱医院,而医院的班都排得满满当当,门诊量甚至“赶上2019年的水平”。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孙红英、李来娣、李孝林、王家君、刘佳、钱进为化名。)
本期资深编辑 邢潭